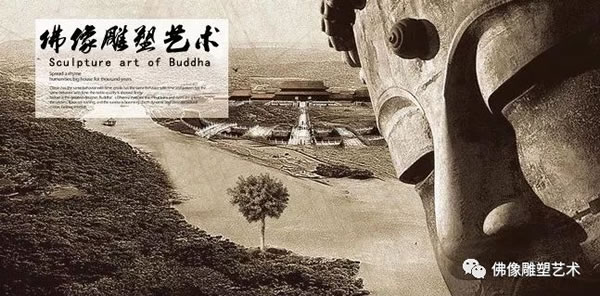

一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绘画增添了取之不尽的新鲜血液。公元1—7世纪是印度佛教艺术的黄金时期,先后诞生了犍陀罗、秣菟罗和笈多等各种艺术式样,且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国,形成了克孜尔石窟、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以及不可胜数的佛教寺庙。依托这些石窟和寺庙的石壁或墙壁,人们绘制了大量的壁画,同时还在纸、绢等材料上创作了无数的卷轴画。佛教的诸佛菩萨和诸天罗汉等形象,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题材,促进了该画种的发展。特别是焦点透视和凹凸晕染法等绘画技巧的传入,改变了中国画“古画皆略”的不足,使人物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具有现实感和真实感,并能营构同一空间由众多人物组合而成的宏大场面,这是之前的单幅画所无法比拟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做过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绝大多数画家都画过佛教题材的绘画,如卫协、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宗炳、张僧繇、曹仲达等。如果从佛教艺术的数量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造诣之深来看,实际从事佛教艺术创作的画家又何止成千上万。宗白华先生称六朝到晚唐宋初的佛教艺术完全可以和希腊的雕塑艺术争辉千古。
后来,随着禅宗的兴起,佛教绘画艺术的整体情况也为之一变。禅宗的教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五灯会元》卷一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碧岩录》第一则评唱道:“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里“直指人心”的“心”即真如、法身、佛性,也被称为“本来面目”,即“父母未生时”的本来状态。这种“本来面目”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把握的,而必须诉诸直觉思维——悟。“悟”是超越经验、知识、理性、逻辑的主观体验,是对内在心性的直接感悟,抑或是本有佛性的自然呈现。由于禅以开悟为目的,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必然贬低经典,反对外在的偶像崇拜。在这种氛围下,原先那些用于礼拜的佛教绘画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表达心性为目的的禅画和受禅画影响的文人画。关于这种转变,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曾做过简明扼要的说明:“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以来,佛教与吾国的绘画,极是相依而生活,相携而发展……。”他认为,“唐以前的绘画,为佛氏传教的工具;唐以后的绘画,为佛氏解悟的材料而不同罢了。”在潘先生看来,唐之前的佛教绘画和文字版的经藏一样,是宣教的工具;而在唐代禅宗兴起之后,绘画则成了禅僧们表达自己内心感悟的手段。从题材来讲,禅宗绘画不仅有诸佛菩萨、诸天罗汉,还包括历代祖师、著名居士的画像以及禅宗故事,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画像赞。由于禅画的重点在于“表达自己内心感悟”,所以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随情而造”。道宣说:“今人随情而造,不追本实,得在信敬,失在法式。”“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我们看贯休、梁楷等人笔下的祖师、罗汉像,确实是在写他们心中的感悟了。
二
“不立文字”作用于禅宗绘画,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禅宗绘画虽然汗牛充栋,围绕禅画的像赞、偈颂数不胜数,但很多禅师却对绘画能否如实反映本体,即人的“本来面目”表示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即绘画这种艺术的“言”不能真正表达“本来面目”这个内在的“意”。
《坛经》曾记载蜀僧方辩为慧能“塑就真身”,且“曲尽其妙”,但慧能却说:“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显然慧能认为塑像(理应包括画像)是不能表达人的法身、法性、佛性或本来面目的。关于“法身”,马祖道一曾做过论述:“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样的“法身”无法诉诸具体的形象。黄檗希运对这个本体的“心”也作过描述:“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这样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是绘画所不能表达的。《五灯会元》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马祖道一的法嗣盘山宝积“将顺世,告众曰:‘有人邈得吾真否?’众将所写真呈上,皆不契师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师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师曰:‘这汉向后掣风狂去在!’师乃奄化。”宝积对所有用画笔画出来的像都不满意,原因是本体不可描绘,而普化的“打筋斗而出”是不着痕迹的比喻,反倒被他认可。
宋代临济宗黄龙派初祖黄龙慧南在真赞中说:“禅人图吾真,请吾赞。噫!图之既错,赞之更乖。……谓吾之真,乃吾之贼。吾真非状,吾貌匪扬。”可见,黄龙慧南对丹青表达本体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他的弟子仰山行伟也说:“直饶丹青处士,笔头上画出青山绿水、夹竹桃花,只是相似模样。设使石匠锥头,钻出群羊走兽,也是相似模样。若是真模样,任是处士石匠,无你下手处。诸人要见,须是著眼始得。”行伟还自题其像说:“吾真难邈,斑斑驳驳。拟欲安排,下笔便错。”行伟提出了“相似模样”和“真模样”两个概念,“真模样”是“本来面目”,绘画只能停留在“相似模样”的层面上。宋临济宗僧人印肃说得很直白:“法身非相,安可以泥像丹青。法界弥纶,何必造银楼金屋。”宋僧智愚也说:“道不可传,貌不可绘。”他认为祖师“厚重如山,宽大如海。丹青有神,莫拟其踪。僧繇笔妙,难状其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汝州叶县广教省禅师,他强调:“我师之真,何用丹青。形如满月,遍布乾坤。”他讲得很明白:“吾真非假,图画非真。”有人请宏智正觉为写真题赞,正觉便写了“说也说不破,画也画不成”、“邈之不真,传之不神”、“像取模画,人成幻化”这样几句话,教人不要执着。临济宗僧人无门慧开感叹说:“时人不识自家佛,却向丹青画处寻。”
元代和明代禅僧显然继承了宋代僧人们的观点,如元初曹洞宗僧从伦在赞文中说:“本来面目妍丑难评,费尽丹青莫能传写。”又说:“世间无限丹青手,到了终须画不成。”同时代的大欣禅师在《题殷济川画》中说:“殷济川画达摩、宝公而下禅宗散圣者凡廿八人,并取其平日机用摩写之。”“然南泉斩猫、雪峰辊球,盖其一时示人,如石火电光,不可凑泊;心思路绝,语默俱丧;况可以笔墨形容哉!画者正郢人误书举烛,而燕相尚明,国虽治而非书意也。”在大欣看来,公案、禅机、悟境也是绘画所不能描摹的。
明僧景隆认为,人的“本来面目”,禅的“活卓之机”,“任是张僧繇、吴道子,尽力描貌不得”。可是世人却不这样,“此意明明妙不传,犹把丹青描这个。”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是徒劳的,是“又将五彩画虚空,大似钵盂安把柄。”明僧颛愚观衡觉得,既然“本来面目自平常,大道不著于言象”,那么即使“者个也说描得像,那个也说描得像,任你描得颛愚十分像,也只描得颛愚之皮肤,终不能描得颛愚之心肝五脏”。明末曹洞宗僧人明雪说:“依真画像像非真,从像显真真非实。非实非真两皆幻,难描老人真仪质。要识老人面目么,三冬桃瓣随风舞,九夏霜花遍地铺。”“真仪质”如同“三冬桃瓣”、“九夏霜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他感叹道:“堪羡良工笔力精,笔笔全是此个身。虽然眉目咸相似,一点中心难画成。”同期的临济宗僧人通贤在《自赞》中提出“范围模样”这一概念,不外乎也是要说明本体不可描画,画出的一定是失去“本然”的东西。如一禅师在《画像赞》中说得更明白:“描得衲僧巴鼻,失却佛祖爪牙。”他提醒人们:“认取山僧本来面目,勿看身上袈裟。”明末临济宗僧海明也对写真画像表示不满:“谓是老僧像,全然都不相。若将作影响,欲赞返成谤。”他觉得“画又不成,描又不就;恼杀丹青,出吾百丑”的原因是:“无像之相,是名真相。但著点染,已成别样。若得不别,不在丹青笔上。”
有清一代,对绘画艺术表达“本来面目”持否定态度的仍大有人在。禅僧迦陵说:“清奇古怪娘生面,妙笔丹青作么施。者厮十分传得似,依然画虎只成狸。”浮石禅师也说:“从来本体难描画,画出谁知失本然。欲本然,卓卓孤峰独顶天。”弘瀚在《自赞》中说:“是真非象,是相非真。”“七尺之躯,堂堂可羡。踞坐俨然,阿谁不见。更写丹青,云遮日面。”清僧正印曾作《自赞》阐明自己的观点:“个老橛强,到处惹人怨谤。……今被众居士和赃捉败,描作人天模样。纵描得十分像,也只是者边模样。若论那边更那边,饶是王维也描不像。”这里的“者边模样”指世俗世界,“那边更那边”当指彼岸世界,或指禅悟境界。还有一些过激的僧人,视世俗文艺为魔事,只会流转于烦恼深渊,生死苦海。如仪润在《百丈丛林清规正义记》中指出:“近日僧中,竟欲以此见长,甚或留神书画,寄兴琴棋,名为风雅。生死到来,毫无用处。”于是他作出规定:“各宜修道,不得检阅外书,及书画等。”“凡经书笔墨诗偈文字,一切置之高阁,不应重理。”清初临济宗道忞也制定了相关的《规约》:“末法师僧,多不根道,稍能搦管,即从事于斯。废日荒月,惟恨揣摩之未工。苟工矣,则傲倪当世,轻忽上流,……由是追陪俗客,衲衣空闲。身虽出家,心不染道,可不哀哉!”他要求僧人们:“凡僧堂寮舍一切案头,除经论禅策外,世典诗文、诸人染翰,除偈颂外,长歌短句,一概禁绝。如违此约,连案摈出。”
三
不过,禅宗虽然高举着“不立文字”的旗帜,但在禅宗的发展史上却始终“不离文字”。实际上,禅宗讲的“不立文字”是在指出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即语言无法准确地把握主体内在心性,无法表达宇宙的实相和禅悟的终极境界。强调“不立文字”是要人们不执着于文字,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文字,毕竟语言文字还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本来面目”和语言文字的关系正如宋僧圆悟克勤所言:“道本无言,因言显道。”“此事其实不在言句上,亦不离言句中。”
为此,唐、宋以降,也有很多禅僧认为绘画艺术仍不失为认识和把握“本来面目”的工具和途径。唐皎然在《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中说:“长史画神独感神,高步区中无两人。雅而逸,高且真,形生虚无忽可亲。”“吾知真象本非色,此中妙用君心得。苟能下笔合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所谓“感神”指的是创作主体深入观察、体验所描绘对象的内在生命——“神”。而“合神”则是创作主体的内在性情(神)与所描绘对象的“神”相互交融,在双向同构中完成审美创造活动。皎然指出“真象本非色”,即事物之“真”并非其外在的色相,必须把握其内在的“神”。只要做到“合神”,笔墨语言是可以传“道”的。宋代心月禅师认识到绘画的警醒作用,他在《降魔图(并序)》中说:“画师笔端三昧,幻出降魔图,有深旨焉。”所谓深旨,即“破彼幽暗,悉使开眼见明,舍邪归正”,让“观图者”“顿见善恶邪正之念”,分清“孰为佛耶,孰为魔耶”,从而得到“自警”作用。慧洪说:“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庄严身。”在慧洪看来,“庄严身”是可以在“毫端”表现的。
元代禅僧清欲认为绘画可以是求道的工具,他在评价《罗汉图》时说:“聚沙成塔,爪画成佛,不失为入道之渐,况精妙若此乎?”清欲强调通过绘画作品来返观自己的本心,“苟能返观自心之体,广大悉备,四圣六凡,由之建立,三昧六通,由之发现,乾坤日月,江海山川,由之出生,便可掩卷一笑。”元临济宗大慧派禅僧愚庵智及在谈绘画鉴赏时说:“世之览者,徒爱其奇形怪状,精巧入神,孰究道之所存为何如耶!”应当“观其迹,究其道,自觉觉他,勿堕声闻”,“直趣自觉圣智究竟之地。”智及认为,欣赏绘画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内容,而应当探究“道之所存”,“观其迹,究其道”,直接进入“究竟之地”。天如惟则也认识到“佛不自佛,从缘而生”,通过宗教艺术可以“令悟世间万物物物皆佛”,“使人人同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说,以至重重无尽、互互无碍,曰理曰事周法界无一而非佛”的道理。也就是说,“一机之发”、“一像之成”,都能够“致广远之化”。绘画史上,“李伯时画马,有讥之者谓:用心久熟,他日必堕马腹中。于是改画佛菩萨天人之像”。赵孟頫也是如此,“松雪翁初工画马,至晚岁,惟以书经画佛为日课,岂亦如是为戒耶!”在笑隐大欣看来,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至人转物不为物转,华严法界事事无碍。世俗技艺,无非佛事,水鸟树林,咸宣妙法。”
明代禅僧对绘画的作用又有新的认识,既重视画像的教化功能,又突出了绘画的“心”本体。紫柏真可明确指出:“夫画本未画,未画本于自心。故自心欲一画,欲两画,以至千万画,画画皆活,未尝死也。……未画画之母,无心天地万物之祖。既知其母,复得其祖。”“自心”是绘画之“祖”,“未画”是绘画之“母”,画出的“一画”乃至“千万画”则是子孙。“自心”是绘画的本源,是艺术的本体。他在分析吴道子、李公麟的画时说:“唐吴道玄、宋李伯时,皆以画鸣于世,虽风致各臻所妙,然离自心光,皆无所施其巧焉。予以是知二子者,皆以道寓技者也。”吴道子、李公麟的画之所以达到了特别高的境界,原因在于他们都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心光”,他俩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以道寓技”,所以达到了道的高度。由“以道寓技”出发,紫柏真可进一步提出佛祖画像的作用在于“即像道存”,也就是“由道影而识诸祖,由诸祖而辨道场,由道场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测虚空,由虚空以悟自心者,可谓寻流而得源矣”。正因为佛教绘画让信众“寻流得源”,所以才会有“圣人设教,大觉垂形”,借此来“开众生本有之心,熏发本具之善”。“圣人形化而影留,使天下后世,即影得形,即形得心,即心复性。”真可还将这种“寻流得源”的认识路线概括为“善返”,他指出:“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返者,由影得形,由形得心,由心得道。”“善返”说为绘画与“本来面目”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与紫柏真可同一时期的禅僧憨山德清也强调“心”在绘画创作中的本体地位。他在《送仰崖庆讲主画诸祖道影序》中说:“心如工画师,画出诸形象。”画家笔下的各种形象都是“心”的产物,都是由“心”幻化而成。德清的观点有时有点自我矛盾,比如他一方面认为,“夫形像可画,而神通妙用,及度生事业,又安得而画之哉?”(《送仰崖庆讲主画诸佛道影序》)另一方面又认为,“欲观微妙身,故借画工手。”而且“画工与大士,同入不思议。影现一毫端,如春在百花。于最微妙中,全体一齐现。”(《天衣观音大士赞》)关于佛像的作用,德清说:“伏以法身非相,托有相以明心”(《造旃檀香佛疏》),即无相的“法身”是要通过有相的绘画来显现。“今之庄严此像,匪直饬金木之幻形,实所以开自心之佛性也。”(《庐山万寿寺庄严佛像记》)雕塑或绘制佛像的目的是要开发修道者自心中的佛性,因为“睹像教以兴心,用庄严而表法”,通过“见闻瞻仰”,来达到“同出迷途”之目的。(《造旃檀香佛疏》)他强调,只要“令观者心存目想”,就可以“即此五蕴幻妄身心,于一念顷,顿见本真”。(《旃檀香如来藏因缘记并赞》)
明代禅师除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外,还有不少人对绘画与“本来面目”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法杲在谈到甘塑师的作品时说:“甘塑师技进也,分华布彩从心写。”肯定了甘塑师的作品是“心”的产物。临济宗僧古雪哲说:“吾佛之教,权实并行,理事无碍,故一瞻一礼,一香一华,或绘或雕,或塑或铸,或赞叹,或恭敬,皆获成佛。”“由此观之,遵佛之训,事佛之像,成佛可立而待也,又岂特天人福报而已哉!”古雪哲肯定了造像是“成佛”之道,而且是“可立而待”。释莲如在《画禅》中辑录了自南齐释惠觉至元代雪窗共64位画僧的事迹,认为这些画僧“皆僧林巨擘”,这些杰出的画作“盖无适而非说法也。”“其游戏绘事,令人心目清凉。”这就是所谓的以画寓法、以画说法。明末如一禅师在《佛祖正印源流图像赞序》中说:“昔公美观断际仪像,而直下顿醒;高峰读五祖真赞,而打破疑团。”根据这些实例,如一禅师肯定道:“所謂色相語言,皆归第一义谛,信不诬矣。”如一还说:“可传者影也,不可傳者心也。”“因影而会心,忘心而契道。”这里的“会心”、“忘心”和真可的“善返”说是一致的。同时期的曹洞宗僧净斯认为:“众生迷于声色,汩于轮回,外逐妄境,内惑真性”,而造像可以“使人礼其相而契无相之法身,瞻其形而获无形之妙用,不假修证,始知本来是佛。”
禅僧元贤也高举“悬象以立教”的大旗,主张“由像契心,优入觉域”。关于“象”与“心”的关系,他主张“立象以尽意”,“忘象以明心”。因为“象不立则意弗尽,象不忘则心弗明。故未有不由象而入,亦未有不忘象而得者。”元贤还说,观赏佛祖菩萨画像,不应当“徒瞻仰于形似之间,探寻于糟粕之末”,否则便有“买椟还珠之诮”。正确的方法是:“因影而求其真,因可传而行其不可传。”
清僧道霈曾谈及“法身”与绘画的关系:“尝观佛祖众生亲从法身方现起,都是个影子。而丹青者,又于影上现影。虽展转虚寂,要之真本无影,而影不离真,总以法身为定量,惟在智者能深自观耳。”佛祖众生已是个影,描绘佛祖众生的画像更是影上现影。但是,这个影上现影也有其重要作用,“盖所可得而传者影,不可得而传者非影。苟有因其可传而得其不可传,则所谓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者,岂虚语哉?”通过画像这个影可以得到非影,亦即本来面目,这是禅宗艺术观的一大进步。为此,道霈充分肯定像教的作用,“唯赖像教,以启迪群迷”,“是知造佛,乃成佛之缘,不独为人天福报而已。”道霈在《鼓山诸祖道影记》中说:“诸祖既往,而仪表如生,智者若能睹其影而见其形,见其形而见其心,则诸祖不先,我等不后,即是亲依座下,亲聆謦咳,亲领棒喝,岂古今时处所能间隔耶?”
以上是禅宗绘画史上有关绘画艺术能否表现人的“本来面目”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文字观在绘画领域中的反映。从时间上来讲,上自中晚唐,下至明清,可谓旷日持久。虽然讨论的双方最终也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却深化了人们对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别是对绘画本体论、绘画创作论和绘画鉴赏论的认识,因而有其积极意义。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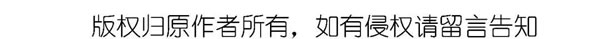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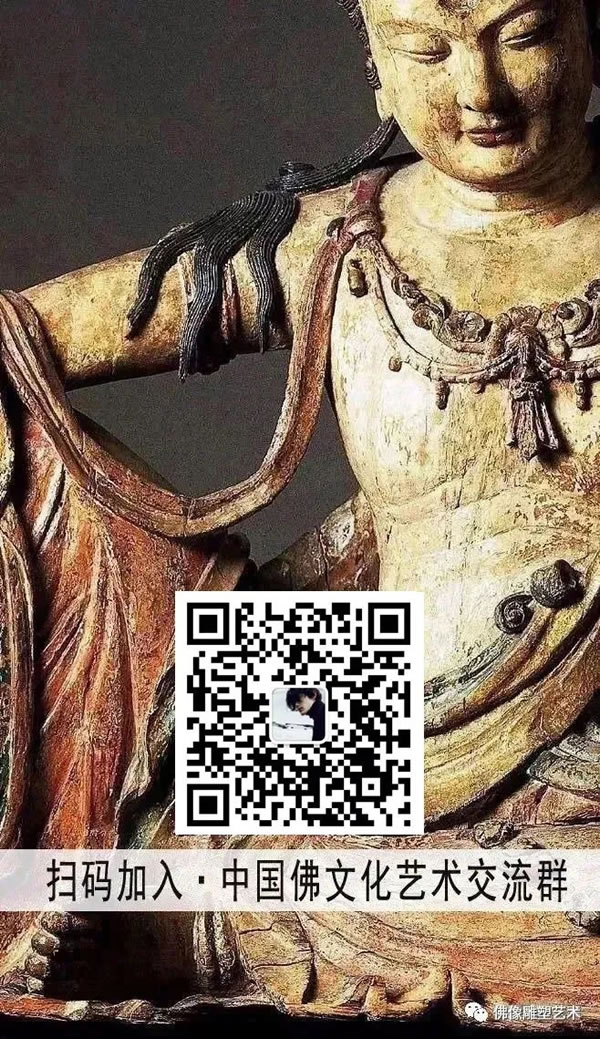
长按关注:[佛像雕塑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