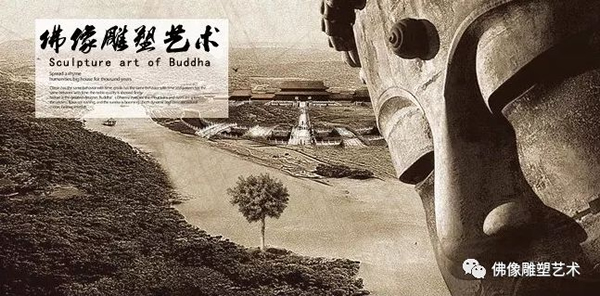

220窟的《帝王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充满想象力的佛国世界中,巨佛位居后侧,前方立于毯上并且最显眼的是身着华服的几名舞者,身姿轻盈矫健,挥着长巾旋转如疾风,两侧的乐队应和着节奏。
这是敦煌莫高窟220窟北壁的一幅壁画《药师经变·对舞》,画中所绘正是在唐代风靡的胡旋舞,绚丽的色彩和高超的技艺将神思牵引回久远的盛唐。
这个“传奇洞窟”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称之为上乘之作,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就曾表示,其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画。
220洞窟里的惊人之作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一次偶然发掘,常书鸿先生领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洞窟进行清理,在清理到220窟的时候,拂去经年的尘土后,工作人员发现壁画脱落的一角内里显现出鲜明的色彩,这是一幅双层壁画。他们小心翼翼将表层宋绘千佛剥离,竟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初唐壁画。

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勘察洞窟
一般来说,里层保存完整的双层壁画实在是难得一见。古人在前代人遗迹上绘画时,很少会考虑到覆盖遗迹所带来的破坏,因此采用的工艺通常需要把前代的壁画打磨成更有摩擦力的平面。但220窟的双层壁画内层被揭开后仍然保持完好,得以让后世的人一窥其艺术风貌。
220窟留下的众多迷思里,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洞窟到底是由谁修建的?为什么这些壁画艺术会出现在大漠戈壁中?
与很多西方艺术赞助制度相似,敦煌石窟修建也依赖于物质资金等赞助,而出资的赞助人也从每个洞窟的供养人壁画中得以考证。
什么是供养人呢?供养人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因为信奉某种宗教提供了资金、劳力来支持洞窟修建,或者以崇敬、赞叹、礼拜等精神性活动来供养佛教。从物质层面来看,供养人就是这些洞窟得以开凿的“金主”。供养人往往会让画匠把自己和家族的画像绘于洞壁之上,向佛祖表明自己和家族供奉的虔诚之心和修窟建佛的功德,同时也祈求神佛能给予家族以庇佑。

莫高窟第130窟 都督夫人供养像
段文杰临摹
吴健摄敦煌研究院供图
士族:220窟背后“金主”是谁?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三联中读音频节目《了不起的敦煌》主讲人之一的张先堂曾在莫高窟做过调查统计,目前保存有供养人画像的就有281窟,占到了莫高窟总窟数的三分之二,保存的供养人画像就有九千多身,跨越了11个朝代。
这些画像也成为了后世研究敦煌供养人制度和家族史提供了图像文献史料,堪称“墙壁上的博物馆”,在供养人图像的身形旁有一条长方形题榜,题写着供养人的名字、官职、功德等信息,也能窥得洞窟开凿的起因。
220窟甬道北壁有一副《翟奉达家族供养像》,上面绘着几个有官阶样貌的人物,依次排列站立。翟奉达是谁?翟氏家族又在220窟的修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幅供养人画像和题记解答了传奇洞窟最初修建的谜题

220窟的翟奉达家族供养像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世家大族是中国从东汉到隋唐一直沿袭的一种家庭组织形式,士族成员多为出仕者,门风优良,一些士族甚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垄断了当地的权力。在敦煌,索氏、阴氏、翟氏、曹氏等都是当地名门望族。
翟氏家族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陈菊霞的研究重点,她也在《了不起的敦煌》中承担了壁画神佛元素一讲的内容。据她介绍,翟奉达是五代时期沙州曹氏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官职为节度押衙参谋,大致等同于现在的处级官员,此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历法家,敦煌的很多历书都出自他手。
南北朝时期,翟家势力开始在敦煌扎根,因为某一陇西翟氏成员“从官流沙”,其子孙从此世居敦煌。通过与敦煌几个士族的联姻,翟氏家族在敦煌的势力迅速扩张。士族中名人辈出,除了翟奉达这样的人物,其他的一些家族成员还在政府机构与军衙中身居要职。
早在西晋的时候,一位名为竺法护的高僧出现在敦煌,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人称“敦煌菩萨”。到了魏晋南北朝,僧伽或教团传教求法,在此地译经讲道,东西往来,日益频繁的流动促成了佛事佛风在敦煌大为盛行,因此也就有了大家族带领下的修窟造像活动。
翟氏也不例外,翟家世代信奉佛教,也热衷于修建佛窟。在北周的时候,翟迁曾在莫高窟修圣容立像。220窟的甬道南壁西侧是翟奉达写的《检家谱》,其中提到了翟家的一位后人,也就是翟奉达的八代远祖翟通,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其官职记载为“诏议郎,敦煌郡博士”,这位翟通大人正是220窟的初始建造者,曾经还在敦煌城修建城塔。但是在220窟的功德碑《翟直碑》中记载道,翟通在此窟修建的中途就仙逝,接下修建大业的正是其子——荣任“伊吾郡司马”的翟直。

《翟直碑》
300多年的时间里,翟氏家族一直持续在营造和重修“翟家窟”。220窟的供养人除了翟直,《翟直碑》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中还提到了他的兄弟辈和儿侄媳等人。到了翟奉达这辈,220窟又被重修,在其记叙的《重修愿文并颂》中提到,重修的目的是为先人造窟的亡灵和过往的族人祈愿。
姻亲:家族的势力网络如何扩张?
像翟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不仅将修窟造像看作是向神佛祈愿和积攒功德的精神寄托,这些洞窟更是成为了当时世家展示家族势力的炫耀性产物。
西方的艺术赞助里,艺术作品与“雇主”的阶级地位和审美趣味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艺术中的供养人制度也不外乎如此,洞窟的形制、壁画偏好归因于其供养人的政治官阶、宗族关系等企图。
在翟家的众多名望联姻中,值得一提的是翟氏与曹氏两家的姻亲。唐朝灭亡后,以曹议金为首的沙洲地方政权执掌者,先后统治一百多年,曹氏家族拉拢回鹘、于阗等周边国,又和敦煌的其他士族结为姻亲关系,通过修建佛窟维护在当地的统治。
在这个出于政治需要所铺设成的庞大婚姻网络中,翟氏成为了曹家节度使政权中的核心力量。曹翟两大家族的姻亲关系,作为宗族可供炫耀的事迹被绘录到了供养人的壁画中。这个时期是敦煌供养人画像最为丰富的时候,也是翟氏家族发展的黄金时期。
到了唐代,除了名气较大的220窟为“洵阳”翟氏所营建,敦煌第85窟则是以得道高僧翟法荣为功德主的“上蔡”翟家赞助修建的洞窟。五代时期85窟重修,供养人画像中的其中一身是曹议金长女,这位嫁到翟家的媳妇就是重修中的功德主之一。为了炫耀翟氏与节度使曹氏的姻亲关系,她将父亲曹议金以及曹氏兄弟的画像都描绘到了甫道南壁,取代原来的供养人画像。

莫高窟第85窟内景
乔兆福摄 敦煌研究院供图
曹议金不仅将长女嫁给了翟氏,还将他的两个儿子都与翟家分别进行联姻。其中第三子,也就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他的唯一夫人就是翟氏夫人,这位翟氏夫人是一位当地的名人,并且极度热爱佛教事业。敦煌的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关于曹元忠与翟氏夫人在佛教法活动的发愿舍施。
榆林第19窟壁画临摹的是曹元忠的画像,而在对面的甬道北壁,便绘着凉国夫人翟氏的画像,画像中翟氏夫人带着步摇,面贴花钿,诠释了何为凤冠霞帔,张大千还曾临摹过这幅壁画为《临摹凉国夫人图轴》。

临摹凉国夫人图轴 张大千 四川博物院藏
翟氏夫人对佛教的信仰不仅对翟家、曹家有巨大影响,甚至带动了周围佛教的发展。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曾认为,晚唐五代敦煌的归义军时期,佛教发展非常平稳,这种平稳不仅归功于曹氏政权下与周边关系的和平稳健,更是由于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推动。莫高窟的大型石窟主要就开凿于这个时期,而曹元忠夫妇的石窟最大也最多,敦煌的一些百姓官吏在修窟造像时,也会将翟氏作为供养人画在石窟的显眼位置。
不仅如此,翟氏还倡导曹家的女性独立营建活动,不依附于家族或丈夫的名义下。莫高窟第61窟南壁同样出现了一副与凉国夫人画像中衣装极为相似的供养人壁画,其中第三身供养人的题记显示,功德主就是“浔阳郡夫人翟氏”。后代学者们根据题记推知,这个窟就是由夫人翟氏供养修建。
在61窟还有一副《回鹘公供养像》。不同的是,以往的供养人都是以辈分高低确定画像中的站位,但在这幅画像中,原本辈分低的回鹘夫人天公主排在前面,嫁给了甘州回鹘曹议金的女儿排在了第二身像,而曹元忠的生母也就是曹议金的原配夫人宋氏被排在了第四位,足以见曹家处于政治考虑对回鹘联姻关系的重视。
人神:佛教世俗化的另类表达
权贵们通过洞窟建造的精美来彰显家族显赫的财力,同时也是他们婚姻网络和既得利益的见证。随着供养人制度的发展,洞窟不再仅仅是公共礼佛的场所,而是具备了更加家族化、私人化的“家窟”意义,这也佐证了唐代的佛教艺术越来越往世俗化、社会化的意义发展。

130窟内有莫高窟的第二大佛
吴健摄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佛教的社会化过程里中,供养人画像不仅与官阶与家族力量紧密关联,也是人窟关系和人神关系发生变化的载体。
根据敦煌供养人的题记,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出现了供养人活动。北凉到隋代的供养人画得都很小,只有十到二十厘米,人物画像很朴拙,仅仅是一个轮廓。最初的供养目的也很简单虔诚,题记也只是寥寥数语指向“一心供养”之意。
到唐代中后期,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到极盛,供养人的地位也由此强化,不仅出现了真人等身大小的供养人画像,画像中人物的面相也趋于清晰。尤其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画像整体场面宏大,构思、技法、颜色都独具匠心。与此同时,画像的位置从龛下和主题画下转移至了甬道两侧的壁画上。
佛窟的性质也向家窟过渡,供养人先亡长辈像也开始出现在石窟中的东壁等重要显眼的位置上。220窟主室西壁龛下赫然写着“翟家窟”三个大字,自此之后敦煌佛窟多以家窟冠以名号,家庙祠堂的意义超越了虔心供养礼佛的初衷。
到了五代、宋时期,供养人的画像进入了洞窟洞壁和甬道两侧,此时的供养人画像已不再单属于一家一族,而是覆盖了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体现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个时期,敦煌由于地处偏远,地方政权逐渐膨胀,已经脱离中原政权的约束。
曹议金就号称是“托西大王”,曹氏归义军时期,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供养人画像也是由世家成员组成的超身大像。张氏、翟氏等家族在重修北魏功德窟时,也就是现在的第437窟,把曹氏归义军长官及其夫人画在了供养人像的中心位。
供养人画像、供养人题记所表现出奉佛供养之意越来越淡,供养制度逐渐走向世俗化,画像表现个人和家族权势以及社会政治联系的味道则越来越浓。由于供养人规模的扩大和供养人制度的发展,此时在洞窟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神”的形象,反而是“人”的形象,佛教艺术从此也更加向着现实与人间。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
阿弥陀经变之化生童子
孙志军摄 敦煌研究院供图
图文来源丨大观日知录
【独冠天下】系列·新书首发|预售

[马上抢购,限时6.6折购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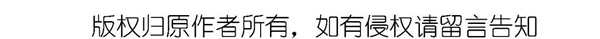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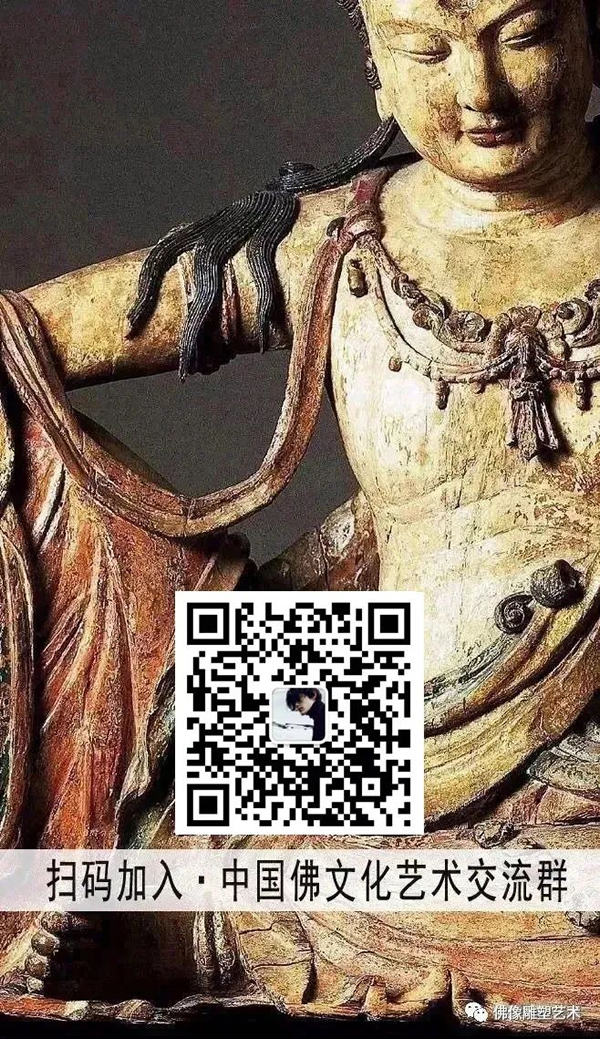
长按关注:[佛像雕塑艺术]
